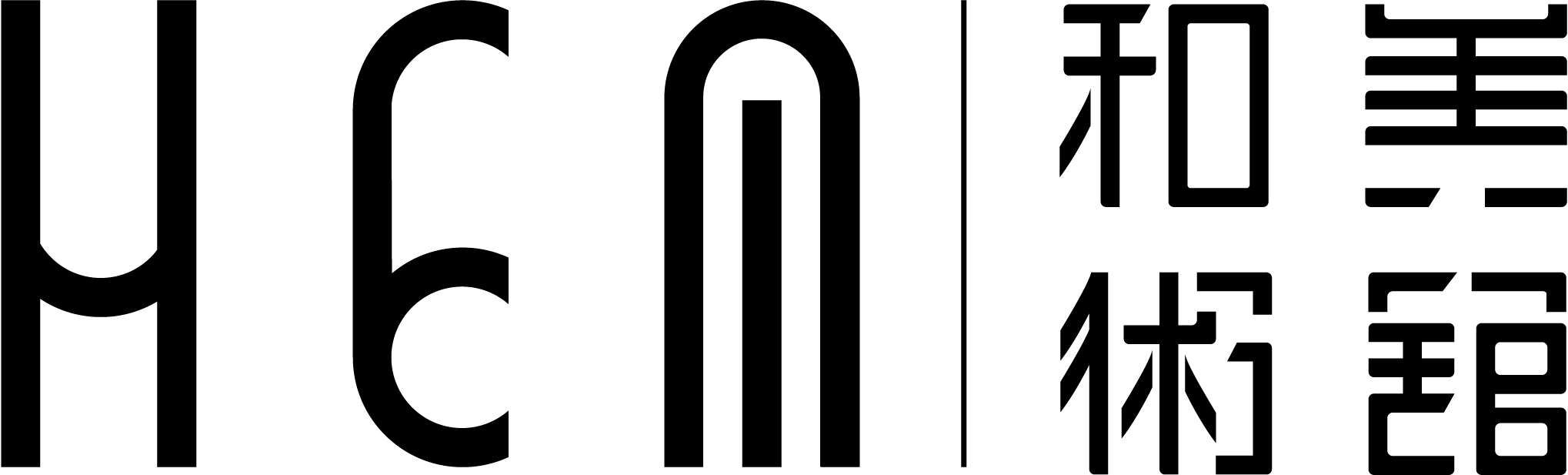概况
距离一九四九年举家搬离都柏林,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。
肖恩·斯库利身穿白色工作服站在画布前,左手提着颜料桶,右手握住笔刷。他画画时一言不发,身体有节奏地晃动着,很难说清是手腕带动身体,还是身体驱动手腕。过一会儿他停下来,稍稍退后几步,用手帕擦脸,然后定睛看着刚刚画上的色块。
他将另一个色块画在刚刚那个的下方,随着手腕的摆动,它们的边缘变得模糊,每一次都改变着边缘的纹理。两个色块彼此亲抚、交战、和解、分离,随后更多色块加入进来。仿佛洋流交汇。色块与条纹都是真正的实体,肖恩·斯库利将之视为世界与情感永恒波动的证据,五十年来他一直在画它们。有时候一个炙热的红,落日或者火焰,会被处理成天蓝色或者祖母绿吗,没有人确切知道,创作是时间的谜底。
他已经去过太多地方,抽象是生命的流放。童年时代在吉普赛人的家里避难,在伦敦的几个贫民窟辗转流浪,祖母的歌声散落其间——“当爱尔兰人的眼睛微笑,清泉也随之流淌”。后来,在摩洛哥、墨西哥或者巴塞罗那,以都柏林濒临潮汐的眼睛,他描述那里轻柔的光线与无垠的夜色。情动的色块以绘画或者雕塑的形式堆叠,如此自治,轻视重力。
肖恩·斯库利来过中国多次,通常是更北的地方。他的作品如今终于深入南方的腹地。在和美术馆,绘画与雕塑中的色彩会随着日光的厚薄泛起或浅或深的涟漪。人们将目光投掷,如同投石子入海。
肖恩·斯库利身穿白色工作服站在画布前,左手提着颜料桶,右手握住笔刷。他画画时一言不发,身体有节奏地晃动着,很难说清是手腕带动身体,还是身体驱动手腕。过一会儿他停下来,稍稍退后几步,用手帕擦脸,然后定睛看着刚刚画上的色块。
他将另一个色块画在刚刚那个的下方,随着手腕的摆动,它们的边缘变得模糊,每一次都改变着边缘的纹理。两个色块彼此亲抚、交战、和解、分离,随后更多色块加入进来。仿佛洋流交汇。色块与条纹都是真正的实体,肖恩·斯库利将之视为世界与情感永恒波动的证据,五十年来他一直在画它们。有时候一个炙热的红,落日或者火焰,会被处理成天蓝色或者祖母绿吗,没有人确切知道,创作是时间的谜底。
他已经去过太多地方,抽象是生命的流放。童年时代在吉普赛人的家里避难,在伦敦的几个贫民窟辗转流浪,祖母的歌声散落其间——“当爱尔兰人的眼睛微笑,清泉也随之流淌”。后来,在摩洛哥、墨西哥或者巴塞罗那,以都柏林濒临潮汐的眼睛,他描述那里轻柔的光线与无垠的夜色。情动的色块以绘画或者雕塑的形式堆叠,如此自治,轻视重力。
肖恩·斯库利来过中国多次,通常是更北的地方。他的作品如今终于深入南方的腹地。在和美术馆,绘画与雕塑中的色彩会随着日光的厚薄泛起或浅或深的涟漪。人们将目光投掷,如同投石子入海。